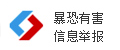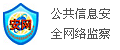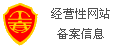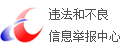|

一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,李白确实是一个不朽的存在。这不仅由于他是一位负有世界声誉的潇洒绝尘的诗仙,那些雄奇、奔放、瑰丽、飘逸的千秋绝唱生发出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;而且,因为他是一位体现着人类个体生命的庄严性、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。 他一生被登龙入仕、经国济民的渴望纠缠着,却困踬穷途,始终不能如愿,因而陷于强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郁与熬煎之中。而“蚌病成珠”,这种郁结与忧煎恰恰成为那些天崩地坼、裂肺摧肝的杰作的不竭的源泉。 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李白,一方面是诗意存在的李白。其间的巨大反差,形成了强烈的内在冲突,凸显为试图超越却又无法超越,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的无奈,展示着深刻的悲剧精神和人的自身的有限性。 李白的心路历程及其穷通际遇所带来的苦乐酸甜,在很大程度上映现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心态。 二 《侯鲭录》载:唐开元年间,诗仙进谒宰相,擎着书有“海上钓鳌客李白”的手版。宰相问道:“先生临沧海,钓巨鳌,以何物为钩线?” 答曰:“以风浪逸其情,乾坤纵其志,以虹霓为丝,明月为钩。” 又问:“以何物为饵?” 答曰:“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。” 宰相闻之悚然。 几句简单的答问,生动而真实地描画出李白的高蹈、超拔、狂肆的精神世界。 这种精神风貌以及他的诗文内涵,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晶。清代诗人龚自珍认为,李白是并庄、屈以为心,合儒、仙、侠以为气的。他那飘逸绝尘、驱遣万象的诗风,显然肇源于《庄子》和《离骚》。而屈原的激浊扬清,治国泽民的宏伟抱负,庄周的浮云富贵、藐视权豪,摆脱传统束缚、张扬主体意识的精神追求,对于李白价值观的形成,影响至为深远。除了儒、道两家为主导因素,在李白身上,游侠、神仙、佛禅的影子也同时存在。 本来,唐代以前,儒、道、释以及仙、侠诸多方面文化,均已陆续出现,并日臻成熟;但是,很少有哪一位诗人能够将它们交融互汇于个人的实际生活。只有李白——这位主要活动于文化空气异常活跃的开元、天宝年间的伟大诗人,将它们集于一身,完成了多元文化的综合、汇聚。 当然,这里也映现了盛唐文明涵融万汇、兼容并蓄的博大气魄和时代精神。正如嵇康、阮籍等人的精神风貌反映了“魏晋风度”一样,李白的精神风貌也折射出盛唐社会特别是盛唐士子所特有的丰神、气度,这是盛唐气象在精神生活方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 三 我们固然不能因为李白有过“吟诗作赋北窗里,万言不值一杯水”的诗句,就简单地断定他并不看重立言;但比较起来,在“三不朽”中,他所奉为人生至上、兢兢以求的,确实还是立功与立德。既然如此,那他为了能够经邦济世,治国安民,以期创制垂法,惠泽无穷,就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势。为此,他热切地期待着:“长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海”,时刻渴望着登龙门,摄魏阙,据高位。但这个愿望,对他来说,不过是甜蜜蜜的梦想。他的整个一生历尽了坎坷,充满着矛盾,交织着生命的冲撞、挣扎和成败翻覆的焦灼、痛苦。从这个角度看,他又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悲剧人物。 他自视极高,尝以搏击云天、气凌穹宇的大鹏自况:“大鹏一日同风起,抟摇直上九万里。假令风歇时下来,犹能簸却沧溟水。”认为自己是凤凰:“耻将鸡并食,长与凤为群。一击九千仞,相期凌紫氛”。与这种极度自负的傲气形成鲜明对照的,是他对历史上那些建不世之功、创回天伟业,充分实现其自我价值的杰出人物,则拳拳服膺,倾心仰慕,特别是对他们崛起于草泽之间,风虎云龙,君臣合契,终于奇才大展的际遇,更是由衷地歆羡。 他确信,只要能够幸遇明主,身居枢要,大柄在手,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。在他看来,这一切作为与创作诗文并无本质的差异,同样能够“日试万言,倚马可待”。显而易见,他的这些宏誓大愿,多半是基于情感的蒸腾,无非是诗性情怀,意气用事,而缺乏设身处地、切合实际的构想;并且,对于政治斗争所要担承的风险和可能遇到的颠折,也缺乏透彻的认识,当然更谈不上有足够的思想准备。 四 李白有过两次从政的经历。 天宝元年秋天,唐玄宗下诏征召李白入京。这年李白四十二岁。当时住在安徽南陵的一个山村里,接到喜讯后,他即烹鸡置酒,高歌取醉,乐不可支。告别儿女时,写有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诗句,可谓意气扬扬,踌躇满志。他原以为,此去定可酬其为帝王师、画经纶策的夙愿,不料,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幻想。进京陛见后,只被安排一个翰林院供奉的闲差,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,接之以师礼,委之以重任。 原来,这时的玄宗已经在位三十年,腐朽昏庸,纵情声色,信用奸佞,久疏朝政。看到这些,李白自然极度失望。以他的宏伟抱负和傲岸性格,怎么会接受“以俳优蓄之”的待遇,甘当一个跟在帝王、贵妃身后,赋诗纪盛、歌咏升平的“文学弄臣”呢?但就是这样,也还是“君王虽爱蛾眉好,无奈宫中妒杀人”,“谤言忽生,众口攒毁”。最后的下场是上疏请归,一走了之。在朝仅仅一年又八个月,此后,再没有登过朝堂。 天宝十四载冬天,李白正在江南漫游。是时,安禄山起兵反唐,次年攻陷潼关,玄宗逃往四川。途中下诏,以十六子李璘为四道节度使、江陵郡大都督。野心勃勃的永王李璘,招募将士数万人,以抗敌、平乱为号召,率师东下,实际是要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。对于国家颠危破败,人民流离失所的现状,李白早已感到痛苦和殷忧。恰在此时,永王李璘兵过九江,征李白为幕佐。诗人认为建功立业、报效国家的机会已到,于是,又一次激扬志气,满怀着“欲仰以立事”的决心,在永王身上寄托着重大期望:“诸侯不救河南地,更喜贤王远道来。”以为靖难杀敌、重整金瓯,非斯人莫属。 岂料,报国丹心换来的竟是一场灭顶之灾。他糊里糊涂地卷入了最高统治层争夺皇权的斗争漩涡,结果是玄宗第三子、太子李亨即位,李璘兵败被杀,追随他的党羽多遭刑戮,李白也以附逆罪被窜逐夜郎,险些送了性命。这是李白第二次从政,为时不足三个月。 尽管政治上两遭惨败,但李白是既不肯认输也不愿甘心的,亟欲寻觅机会重抵政坛,锋芒再试。六十一岁这年,他投靠族叔、当涂县令李阳冰,定居于采石矶。虽然已经处于生命的尾声,但当他听到太尉李光弼为讨伐叛将史朝义,带甲百万出征东南的讯息,一时按捺不住心潮的狂涌,便又投书军中,表示“懦夫请缨,冀申一割之用”,无奈中途病还,未偿所愿。 五 表面上看,两番政治上的蹉跌,都是由于客观因素,颇带偶然性质;实际上,李白的性格、气质、识见,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。他是地地道道的诗人气质,情绪冲动,耽于幻想,天真幼稚,放纵不羁,习惯于按照理想化的方案来构建现实,凭借直觉的观察去把握客观世界,因而在分析形势、知人论世、运筹决策方面,常常流于一厢情愿,脱离实际。 剖析李白第一次从政的挫折,一是,本来他就不是摆弄政治的角色。玄宗召他入京,原有几分看重,但很快就发现他并非“廊庙之材”,便只对他的文学才能加以赏识,所以后来他要求离开,也并不着意挽留。二是,李白缺乏政治的眼光。当时,玄宗已不再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开明君主了,而李白却仍然寄厚望于他,最后当然是失望与绝望。 而“从璘”一举,益发暴露其政治上的幼稚。他对“安史之乱”中的全国政局,估计得过于严重,诗中所云:“颇似楚汉时,翻覆无定止”,“三川北虏乱如麻,四海南奔似永嘉”,显然是违反实际的。形势判断失误,行动上必然举措失当。在他看来,当时朝廷应急之策,是退保东南半壁江山,苟延残喘;而永王正好陈兵长江下游,自然可以稳操胜券,收拾残局。这是他毅然“从璘”的真正原因所在。而这一着,他恰恰把“宝”押错了,结果又一次犯下了知人不明的错误——他既未发觉李璘拥兵自重、意在割据的野心,更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刚愎自用,见识短浅,不足以成大事的庸才。把立功报国的希望寄托于这种角色,未免太孟浪了。 看来,一个人的政治抱负同他的政治才能、政治识见并不都是统一的。归根到底,李白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,大概连合格也谈不上。他只是一个诗人,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。虽然他常常以政治家傲然自诩,但他并不具备政治家应有的才能、经验与素质,不善于审时度势,疏于政治斗争的策略与艺术。其后果如何,不问可知。对此,宋人王安石、苏辙、陆游、罗大经等,都曾有所论列。 这种主观与客观严重背离、实践与愿望相互脱节的悲剧现象,在中国历代文人中并不鲜见,值得我们深长思之。 六 之所以出现这种悲剧现象,自然应该归咎于文人的傲睨自诩、自不量力的性格弱点。但若寻根溯源,又和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“修齐治平”的价值取向有直接关系。儒家的祖师爷孔子,终生为求仕行道而四处奔波,席不暇暖,“惶惶如丧家之犬”,在旁人看来本是无法实现的事,他也要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。这种人格精神对于后世的封建士子特别是文人的熏陶,是至为深刻的。 比起李白来,杜甫可能更典型一些。这位大诗人受他的十三世祖杜预的影响很深,他对这位精通战略、博学多才、功勋卓著,有“杜武库”之称的西晋名将备极景仰。三十岁那年,他从齐鲁来到洛阳,曾在首阳山下的杜预墓旁筑舍居留,表示不忘先祖的勋绩和建业垂统、光宗耀祖的雄心。尔后,便进入京城长安,开始其十年困守的生涯,无非是要“立登要路津”,“欲陈济世策”。他曾分别向朝中的许多权贵投诗干谒,请求汲引,但如同李白一样,都以失望而告终。 总共算起来,杜甫真正为官的时间也只有两三年,而且,官卑职小。即便如此,他也仍是刻板、认真,恪尽职守,绝不荒怠王事。在任谏官左拾遗这个从八品官时,他曾频频上疏,痛陈时弊,以致上任不到半个月,就因抗疏营救房琯而触怒了肃宗皇帝。房琯为玄宗朝旧臣,原在伺机清洗之列。而杜甫却不明白个中底细,不懂得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的事体,硬是坚持要任人以贤、惟才是用,书生气十足地和皇帝辩论什么“罪细不宜免大臣”,最后险致杀身之祸,由于宰相大力援救,遭贬了事。这大概又是一个文人当不了官的实例。 当然,作为诗仙,李白解脱苦闷、排遣压抑,宣泄情感、释放潜能,表现欲求、实现自我的最根本的渠道,还是吟诗咏怀。正如清初著名文人金圣叹所说:“诗者,诗人心中之轰然一声雷也。”诗是最具个性特征的文学形式。李白的诗歌往往是主观情思支配客观景物,一切都围绕着“我”的情感转。“当其得意,斗酒百篇”,“但用胸口,一喷即是”。有人统计,在他的千余首诗歌中,出现我、吾、予、余或“李白”、“太白”字样的竟达半数以上,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仅见的。 诗,酒,名山大川,使他的情感能量得到成功的转移,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精神上的重压。但是,际遇的颠折和灵魂的煎熬却又为最终成就伟大诗人夯实了基础。以自我为时空中心的心态,主体意识的张扬,超越现实的价值观同残酷现实的剧烈冲突,构成了他的诗歌创造的心理基因与不竭源泉,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极高的视点、广阔的襟怀、悠远的境界、空前的张力。 就这个意义来说,既是时代造就了伟大的诗人,也是李白自己的性格、自己的个性造就了自己。当然,反过来也可以说,他的悲剧,既是时代悲剧、社会悲剧,也是性格悲剧。 历史很会开玩笑,生生把一个完整的李白劈成了两半:一半是,志不在于为诗为文,最后竟以诗仙、文豪名垂万古,攀上荣誉的巅峰;而另一半是,醒里梦里,时时想着登龙入仕,却坎坷一世,落拓穷途,不断地跌入谷底。
|


 网站首页 > 文化 > 正文
网站首页 > 文化 > 正文